公元805年,卑湿酷热的湖南永州用滂沱的大雨迎来了一位颇负才气的大师。永州太寂寞,瘴气和兽类充斥着山野河泽,唯独缺少智慧的生命和浩荡的人文精神,于是,好像上天有意要安排一位文化使者来开拓永州的蒙昧与蛮荒,柳宗元蹒跚而来。
柳宗元是在经历中唐那场雷霆万钧的变革——"永贞革新"后,从长安被贬到永州这片荒蛮之地的。少有才名的柳宗元在年仅十三岁时,便以一篇辞采飞扬的《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名动长安,待到其二十一岁时,更是在没有通过任何请托的情况下,在长安科举中成功胜出,跻身仅仅三十二人的耀眼榜单,此后更是以火箭般的速度,进入朝廷中枢,成为王叔文主导的"永贞革新"中得力的闯将。然而,这场被柳宗元寄予极大热情的革新,面对一堵堵难以撼动的高墙,仅仅持续了一百多天,便随着顺宗被迫内禅进而不明不白地死去而惨淡收场。被宦官拥立的太子李纯即位后,是为宪宗,由于当初王叔文集团在继承人问题上并没有站在李纯一边,导致即位之后的李纯对王叔文集团采取了疯狂的报复,就在他登基当月,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参军,不久被赐死,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其余八名重要成员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八人先后被贬为边远的八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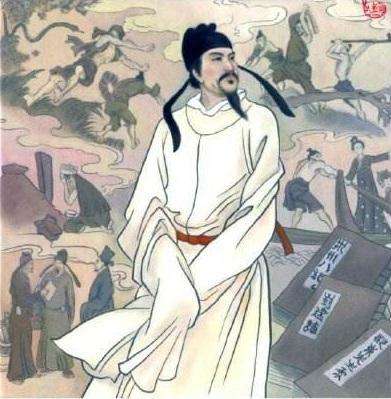
在瞬间由巅峰跌入谷底的八司马中,柳宗元的贬谪之地是相当蛮荒和偏远的湖南永州。柳宗元曾在其《与李翰林建书》中,说"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足见生存环境之恶劣,而作为一场政治改革的失败者,柳宗元的安身立命之所只能是荒僻和不毛之地。皇帝将御笔直指永州,人烟稀少,再有韬略也不足以举事;远离京师,再有才华也不能乱我朝纲,这时再配上一个监视的官员和满眼的崇山峻岭,就锁住了一个中国封建文人的视野和心灵。
如果说,刚刚踏上永州这片土地,柳宗元还带着贬谪之臣的况怨,对永州山水人文并无感情,那么,当禅院的烟霭弥散于一张空白的宣纸之上,当佛国的井水冲涤开诗人封闭的心扉,柳宗元与永州的距离,已经在一点点地拉近。是的,让柳宗元的骨子里融入永州意识的,正是他笃信三十年的佛教。史载,唐时的永州,虽地处偏远,但佛教活动却并不匮乏,南北往来的僧侣都将永州做为暂时的落脚之地,而令人错愕的是,在永州这样一座荒僻小城,竟坐落着大大小小三十六处寺庵禅院,包括柳宗元寄住的龙兴寺在内,华严寺、开元寺、法华寺等,都拥有着众多虔诚的信众。正是在与这些寺院的高僧大德往来之中,心情郁闷的柳宗元找到了生命的出口,寻得了心灵释放的空间。他拜龙兴寺重巽住持为师,时常到其讲经说法的净土院研习佛经,在对佛教精义有了深入了解之后,他仿佛醍醐灌顶,提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进而产生了援佛济儒、统合儒释的设想。"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当在浩荡的梵音中安下心神,当佛国的水汽漉湿渐染斑白的额角,柳宗元拭去感伤的泪痕,,"自肆于山水间",开始重新谛视命运,谛视人生,谛视永州。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江雪》
由此,脍炙人口的《江雪》的横空出世,便顺理成章!这首流传千古的诗歌,垂髫小儿皆能吟诵,历代画师更是借此诗意境,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画卷。按理说,柳宗元的贬所永州,地处湖南的南端,跟本与雪无缘,但上苍好像有意要和柳宗元开个玩笑一样,就在柳宗元来到永州的几年间,旱涝频繁冰冻十分严重,竟然出现了少有的极寒天气,柳宗元在其《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二年冬,幸大雪,逾岭被南越中数州",漫天大雪之中,踽踽独行的柳宗元感受着永州的山寒水瘦,更在对自己的内心进行着观照与自省,他把自己放逐成一个独钓寒江的渔翁,让自己成为大片留白中一个坐如磐石的黑点,而这个孤寂的黑点,恰与一千年前的屈原形成跨越时空的应和,自从"屈原既放,游于江潭"之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渔父意象,便成为中国文人遗世独立清标孤高的标准意象,而将这个意象置于"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荒原大野之中,更显出一个文人的超拔与独立。寒江之上的柳宗元,就是那个划动孤舟的蓑笠翁,彼时,经历了丧母之痛和居所火劫的柳宗元,太需要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覆压住内心的伤痛了,而偏偏永州有情,读懂了诗人,理解了诗人,凛冽的寒风夹带着百年不遇的鹅毛大雪,为诗人铺展开一张洁白干净的"宣纸",这张"宣纸",是永州为柳宗元量身而定,这张"宣纸",摒弃了所有局外之人,只允许柳宗元一人跳进跳出,当柳宗元最终以一首冠绝千古令人"读之便有寒意"的《江雪》,让自己成为永远的画中人,他不会知道,自己已然跨越了小我的悲喜,将人生的骚怨与旷达融入一种超尘拔俗的大孤独之中。

至此,荒僻的永州,终于有了淋漓酣畅的脚步声,那是柳宗元踏察永州山水的脚步,山水永远对应着中国文人的情绪,中国文人困厄感郁,山水也就黯然无光;中国文人激情澎湃,山水也就熠熠生辉。正是在对永州山水的踏察之中,柳宗元才发现,自己与永州的关系,早已不再是初来乍到时的疏离感和陌生感,而是在和山水的亲密接触之间,和永州实现了不可切分的勾连,而最能体现这种关系的,莫过于柳宗元脍炙人口的《永州八记》,正是由于柳宗元的激情书写,永州,才得以于蛮烟瘴雨于之外,以一脉清逸的禅理汇入中国文化的激流。
《永州八记》按写作顺序,依次为《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从这些题目看,摄入诗人笔端的永州山水不过是些土丘石陵,溪流浅洼,但柳宗元却以细腻的观察和灵动的笔触,让永州的山变得奇峰屹立,让永州的水变得空明澄澈,尤其是《小石潭记》,更是将一个不知名的小潭写得气韵生动,出神入化,这是一处"竹树环合,寂寥无人"的人间秘境,又何尝不是柳宗元在与永州消除心理隔膜之后为自己也是为永州营造的一处心灵秘境呢?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
——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节选)
据说写这篇小品之时,柳宗元已由暮鼓晨钟的寺院搬到了愚溪。愚溪原名冉溪,是潇水的最后一条支流,而愚溪这个名字,则是搬迁至此的柳宗元所改,一字之差,自嘲之意尽显,但柳宗元不会想到,这个愚溪的命名,会在此后千年,成为永州人恒久炫耀的标签,而永州本身,也因柳宗元的润色和经营,由一座旷大无比的天然监狱转化成滋养和启迪中国文人心性的圣地。

